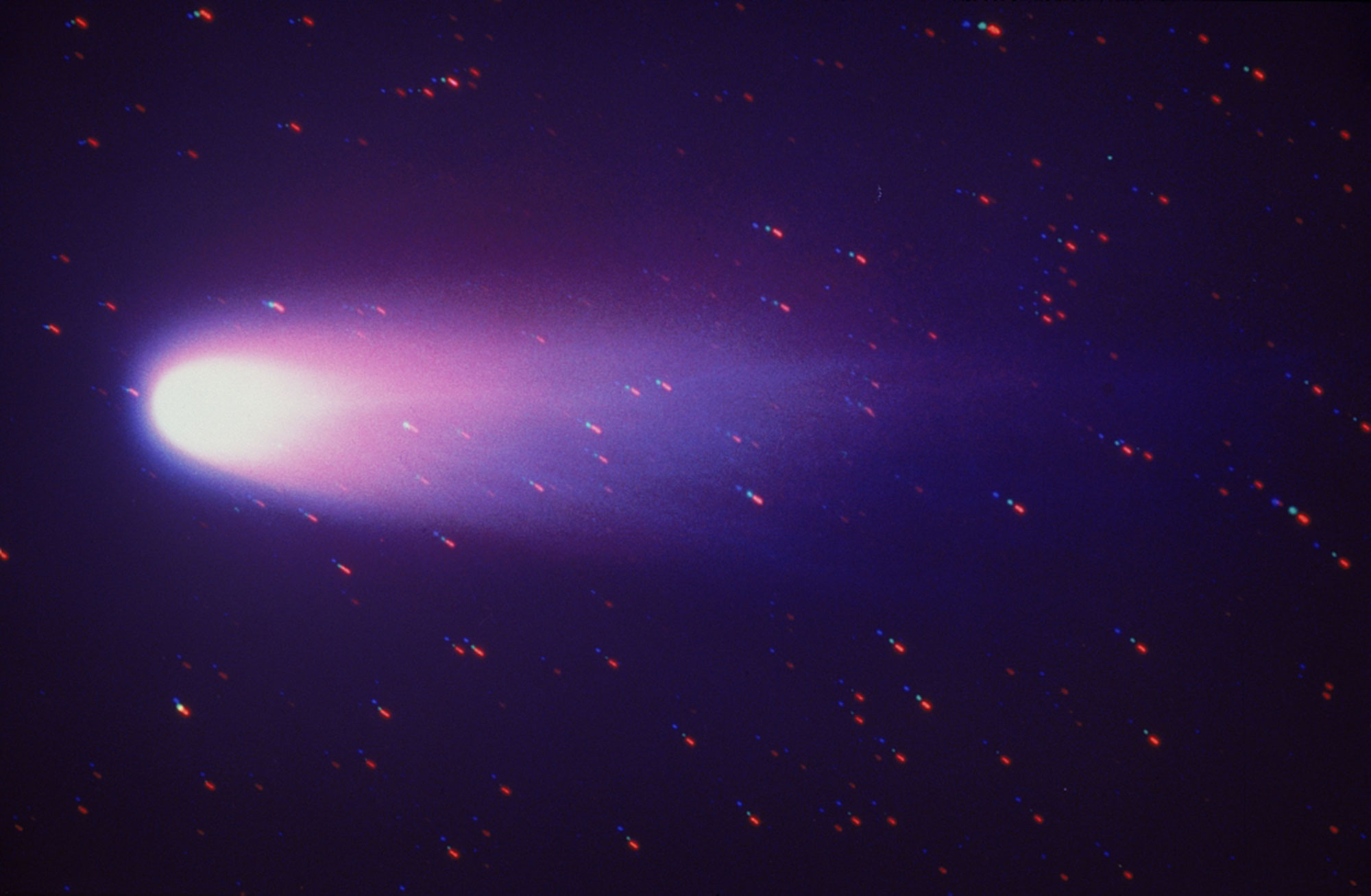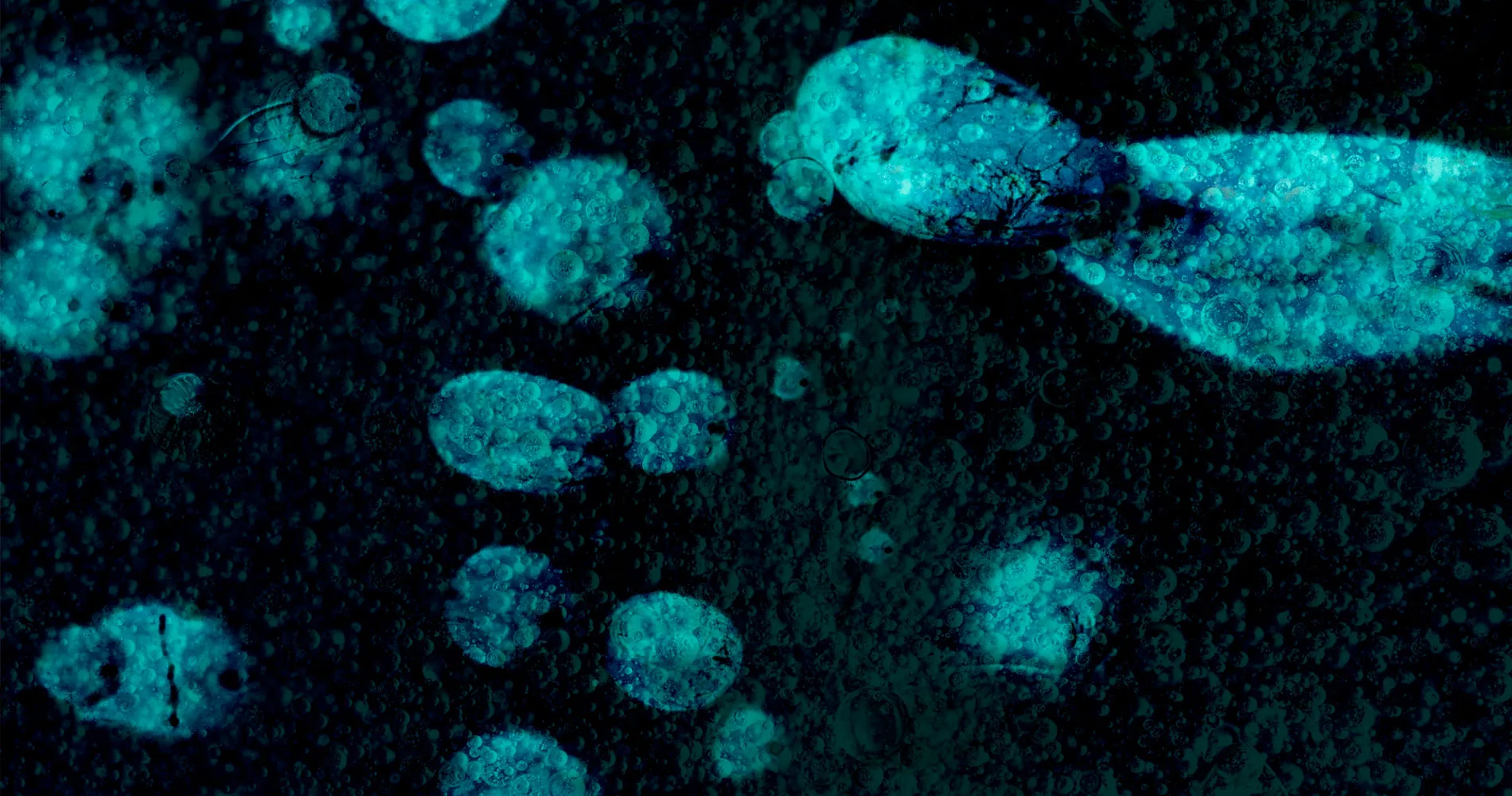23年后,国际刑事法院终于对首位达尔富尔战争罪犯做出判决。然而,截至目前为止,国际刑事法院的所有针对暴行的判决都指向非洲,这加剧了人们对该法院的指责,即法庭只为部分人主持正义,而真正有权势的人则可以逍遥法外。
Michael Asiedu
2025年11月12日
English version | German version
2025年10月6日,国际刑事法院创造了历史。阿里·穆罕默德·阿里·阿卜杜勒·拉赫曼(又名阿里·库沙卜)被指控犯有27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。56名证人向法庭描述了惨无人道的暴行——村庄被夷为平地,大规模处决,强奸被用作恐怖手段。在2003年至2005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冲突期间,多达30万人在达尔富尔丧生。
20年后,受害者们终于听到了“有罪”二字。然而, 与这份胜利相伴而来的,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——所有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犯人都是非洲人。
这些数字令人震惊。自2002年以来被起诉的54人中,有47个是非洲人。该法庭总共判处了11人有罪,但其中,6人犯有核心国际罪行——战争罪和反人类罪。而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、马里和乌干达。难怪批评人士称其为“非洲法庭”。卢旺达总统保罗·卡加梅毫不含糊地指出,该法庭存在的目的就是“起诉非洲人和其他来自贫困国家的人”。前非盟主席让·平的问题则更尖锐:“为什么不是阿根廷?为什么不是缅甸?为什么不是伊拉克?”
这并不是推卸责任。倡导问责制的非洲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也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质疑。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库沙卜是否罪有应得,他的犯罪证据是充分的。问题在于,那些有权有势的非洲犯罪者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清算。
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大胆的行动。2023年3月,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,这是第一份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逮捕令。2024年11月,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·加兰特发出逮捕令,指控他们在加沙犯下的罪行,包括种族灭绝和利用饥饿进行战争。2025年1月,国际刑事法院将矛头指向塔利班领导人,指控他们进行性别迫害。
这些行动展现出了勇气,但也引发了愤怒。美国前总统拜登称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“令人愤怒”。美国参议员林赛·格雷厄姆威胁称,将对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和法国实施制裁,如果他们协助国际刑事法院的话。俄罗斯则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发出了逮捕令。该法院还遭遇了网络攻击和渗透的企图。
但逮捕令不是判决。普京依然可以自由执政,甚至访问过蒙古——蒙古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,拒绝对他进行逮捕。内塔尼亚胡尽管受到限制,但依然在执政。为避开欧洲领空,他的飞行线路更长,以避免在可能执行逮捕令的国家紧急迫降。国际刑事法院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没有自己的警察部队,逮捕行动完全依赖于成员国。
这一弱点也并非新鲜事。2009年因种族灭绝罪被起诉的苏丹前总理阿尔·巴希尔,访问了19个国家,其中9个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——但他毫发无伤。非盟宣布,成员国“不会配合”。巴希尔于2019年被罢免,但他依然身在苏丹,而不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所在地——荷兰海牙。
这些问责的失败引发了“退出潮”。2016年,布隆迪、南非和冈比亚宣布退出《罗马规约》,但后两国又撤回了退出决定。非盟于2017年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“国际刑事法院退出战略”,但最终没有强制要求非盟国家大规模退出。然而,系统性的抵制仍然存在。2025年9月,萨赫勒联盟(马里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)集体退出,并谴责国际刑事法院是“新殖民主义”的工具。他们的协调退出代表着有组织的区域性抵制,而不是孤立的退出。这也表明,国际刑事法院在整个非洲大陆面临着持续的合法性危机。
政治秀的背后,隐藏着资金匮乏的危机。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的预算约为1.87亿美元。自2015年以来,尽管案件数量激增,主要捐助国却坚持预算零增长。目前,该法院正在调查跨越各大洲的16起案件。2024年12月,各成员国批准了2025年1.95亿欧元(2.06亿美元)的拨款,比法院要求的2.02亿欧元(2.13亿美元)少了700万欧元。
长期性的资金不足迫使检察官办公室转向自愿捐款。批评者们警告说,这会导致司法政治化。比如,西方国家反对调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行动。而检察官办公室拨给乌克兰的资源几乎是巴勒斯坦的5倍。这是巧合吗?这种做法令人大跌眼镜。当预算流向与捐助国的倾向一致时,选择性司法的指控就无法被驳斥。
然而,讽刺的是,事实并非如此,许多非洲国家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请求。乌干达、刚果民主共和国、中非共和国等国自愿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介入。当军阀被打击的时候,支持率飙升,而当在任总统面临审查时,则爆发了强烈反对。这表明,批评者反对的并非是问责本身,而是非洲领导人被起诉而西方强权却逍遥法外。
反驳的观点也确实存在。近年来,许多暴行发生在非洲。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和以色列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,这限制了其管辖权。国际法院运行遵循补充原则,仅在国家法院无法或不愿介入时才会介入。富裕的国家可以在国内进行起诉。
但这些技术细节忽略了问题的关键。当每一项定罪都针对非洲国家,当针对西方盟友领导人的逮捕令束之高阁,当预算拨款倾向于调查西方国家的对手时,国际刑事法院就更像是权力政治的工具,而非公正的司法机构。
阿里·库沙卜的定罪带来了真正的正义。他的罪行证据确凿,他曾亲自用斧子将两名男子活活打死,并下令进行大规模处决。国际刑法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追责并承认受害者的苦难。而国际刑事法院将一些原本可能逍遥法外的罪犯绳之以法。
但个别的定罪不能弥合结构性的弊端。国际刑事法院在一个根本不平等的体系里运作,这个体系里,权力决定了哪些罪行会得到调查。除非有一个非非洲人面临定罪,而不仅仅是指控,
“非洲法庭”的标签才有可能去掉。除非强国与弱国承担着同样的责任,否则,新殖民主义的指控将萦绕在每一次指控中。
国际刑事法庭需要三样东西以维持生存——与其职责匹配的可持续的资金,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资金匮乏;能够确保逮捕行动不受权利限制的执法机制;以及能够证明国际法普适原则的起诉。
阿里·库伊卜的定罪证明,对大规模暴行伸张正义是可能的。但对于所有罪犯,无论其国籍或盟友的影响力如何,是否能平等地获得正义,仍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如果法院不取得进步,它就有可能变成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成为强者惩戒弱者的工具,而强者自己却永远不受约束。